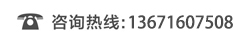在7月初蘇州的一次論壇上,中歐商學院的朱曉明院長委婉地勸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MBA畢業的Uber中國區運營經理汪瑩,“你的下一個職位應該是去美國白宮當新聞發言人而不該是在中國。”
完美的淑女坐姿和熟練的pR技巧并不能幫助這位年輕美貌的MBA在遭遇艱難地詰問時贏得工科男出身的朱院長的贊許:在回答主持人關于“你怕滴滴嗎”這個幾乎必答題的時候,汪小姐給出的答案卻是如何感激政府合作,相信政府會搞定一切云云。
這樣的答案怎么可能讓幾乎培育出了無數中國最好的MBA學生的朱教授滿意?
無數高大上的外資企業在中國市場上暴露出的短板幾乎從來沒有例外過:他們所刻意展現出來的優雅,風趣,甚至是良好的禮儀姿態,并不代表著對客戶和公眾的真心尊重。因為大部分在中國運營的外資企業,還并沒有真正形成能被本土接納的價值觀。
Uber也是一樣。本來這是一家明確地要去顛覆傳統社會的創新公司,它之所以誕生,是因為在巴黎市中心你需要等上1個小時,或者付出100歐元,才能乘坐出租車來到迪斯尼樂園。在共享經濟的大背景下,Uber的出現本來就是最具備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理想色彩的:讓自己的財產和技能隨時都處于云備胎的情景模式下,以換取不受空間和時間束縛的工作場景。
這樣的企業文化實質,使得任何公開的強行跪舔都只能暴露出本地運營人員的急于求成和不接地氣:如果傷害的是全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利益,沒有人會因為幾句刻意的逢迎和積極的表態就網開一面。
關鍵還是看你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Uber在中國實際上和美國有著本質不同。因為在中國,出租車的價格實際上并不昂貴,而人民優布也不見得擁有遠超競爭對手的優勢。在中國,Uber首先要解決的,其實是覆蓋率和應召響應時間的問題。而恰恰在這一點上,Uber做到的確實沒有說的好聽。
2015年Uber在中國據說有入住了14個城市,年底要進軍100個城市。進軍的路線圖大約是這樣的,Uber的后臺會顯示出在一個城市還沒有Uber服務之前,已經有多少個用戶曾經在這個城市打開過了Uber。當這個數量積攢一定的數值之后,Uber總部就會決定進軍這個城市。
這種進軍邏輯就像拿破侖在滑鐵盧戰役上制定的計劃,聽上去無比炫酷,在執行端卻總是錯失良機。滴滴要是按照這樣的打法,估計早被弄死了。且不說在蘇州南京這樣的城市,找到一條Uber并沒有想象中容易,但就說上海這樣的大都市里,Uber就必須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他的司機不認路。
這就是Uber模式的硬傷,在舊金山,也許是導航發達也許是道路簡單信息明了,這樣的弱點并不明顯。但在上海,首先是司機明明只有500米,趕來也要10分鐘的事情屢屢發生,到達預定地點后,確定要去的地方下客又要十分鐘......因為在中國,交通條件過于復雜,而普通司機和職業司機之間的差距往往比想象中要大得多,在上海,到達目的附近2公里后來回掉頭尋找路口的事情屢見不鮮。
在這一點上,本土的專車公司(諸如神州專車)卻擁有不可比擬的優點。統一的制服,良好的經驗,相對較高的薪水和車輛,永遠在線的Wifi,甚至于價格也在“充值100送100”的狀態下變得異常友好。在這一背景下,Uber本來擁有的靈動與價格優勢蕩然無存,尤其是在人們發現傳說中的佟大為林志玲并不常見,瑪莎拉蒂也只是傳說中有實際上最多的是本田的時候,Uber在下一步向三四線城市拓展的時候將面臨更多的窘境:如果文化上的優越感不能兌現,Uber能否有足夠勇氣直面競爭者的沖擊?
中國車輛的清潔程度,駕車者的經驗技術,交通的擁堵繁忙,人們的觀念更新,所有這一切都會超出Uber運營者的想象。更要命的是,如果從交通轉向服務這根本就是中國人的特長。從這一點來講,神州也許是犯了一個公共關系學上的錯誤,卻以前所未有的明確姿態擺清了位置:在中國,Uber的終結者。
也許不是他,但必定在中國。
(鈦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