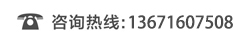你在坐地鐵,廣告在看你,地鐵里流動著各個階層的白日夢想》》》上海公關公司《《《
攝影師張星海喜歡“地鐵是個搖擺的囚籠”的說法。在《北京科技報》工作的他每天早晚高峰要擠地鐵10號線和1號線。他說,地鐵中的廣告就像是籠中鳥的白日夢想圖。畢竟在擁擠的地鐵里,只有在防曬霜廣告上,才能看到瞇著眼睛曬太陽的悠閑自在。
不過對趙罡來說,這個他工作了大半輩子的地方,“根本沒有想象中的那些浪漫事”。在他的印象里,北京地鐵是每一種擁擠可能的總和。在張星海的取景框里,他把這種諷刺的現實和想象中的夢想聚集在同一幅畫面里:
在一度貼著鋪滿整面墻的合家歡月餅廣告的樓梯口,孤獨的老人拄著一根木棍坐在進站臺階上;一個上半身赤裸的醉漢躺在四惠站的過道上,無人過問;一個食堂的小工穿著工服四仰八叉地躺在擠滿人的車廂里,直到終點站被乘務員叫醒,而在他的座位旁邊的廣告位,曾經屬于地鐵沿線“拎包入住”的房地產廣告;還有的時候,在商場周年店慶想象的狂歡節廣告貼紙旁邊,人們因為現實的擁擠大打出手,拳腳相向?
“我的拍攝著眼點是地鐵廣告和經過的人之間的強烈反差。城市里的地鐵早已不止是一種交通工具那么簡單,地鐵成為一種文化,它是一個城市的靈魂。人與地鐵的交錯形成了構造一新的時空。”張星海說,“我感覺地鐵上的廣告就是中產階級價值觀的集中體現,也就是人們向往、熱衷的一種生活方式。但這種生活方式和現實地鐵中的人之間,還存在巨大的鴻溝。”
然而,這些落在廣告紙上的中產階級夢想,對親手制造它的宮關勇來說,卻只是想象中的遙遠關聯。只有一次,陪剛出生的兒子看動畫片,在卡通頻道的廣告里看到了自己曾經印刷的畫面。“平時沒有什么感覺,就那一次覺得??”他想了一會兒,突然笑起來說,“嘿,那可是我做的。”
每天下午5點,地鐵廣告施工隊會把這些承載著迷人夢想的廣告從趙罡的辦公室里帶走。在這兒,地鐵消防常識的貼紙和感冒藥的廣告緊緊地靠在一起,占據一整面墻的手機游戲廣告被扭成一個圈,孤零零地靠在吹出冷氣的空調旁邊,遙望著扔在對面桌子底下的整容廣告,上面寫著大大的兩個字——“知音”。
在它們離開辦公室的路上,壞掉的公交燈箱立在門口,滅了燈的廣告燈箱上還掛著沒換下來的廣告——“別喝太多心靈雞湯,跳槽加薪才是良方。”
4:00AM
凌晨4點,地鐵開始為新一天的旅行做準備。鐵軌旁的電線重新通電,站臺里的照明燈重新亮起來,廣告燈箱里的784盞LED燈也開始重新扮演地下世界里“正午12點的太陽”。
趙罡說,現在環境好些了,工資比過去高,其他待遇也比過去好,就連夜里加班出地鐵,都可以報銷打車回家的錢。可有時候,他還是挺懷念過去的——上世紀90年代,自己還是個業務員的時候,白天到火車站接外地來的廣告客戶,晚上騎一輛紅旗牌的自行車到五棵松貼廣告。下班進胡同,順手抓一棵鄰居家的白菜,就著下點面條跟同事分著吃。“那時候做廣告,講的是‘交往’。”他說。
這種懷舊感情甚至成了廣告的一部分。今年8月,華為手機在北京地鐵1號線做了一次車廂廣告,把整班車貼成“時光專列”,歷數著從1960年代到現在每個十年的經典語句,從“為人民服務”到“哼哼哈嘿”?
“沒有哪種交通工具像地鐵一樣和外部世界隔絕開,地鐵是跟外部世界隔絕的平行世界。在這里,不同階層的人緊密聚集到一起,三教九流的人物云集,抹去一切階級地位。不管你是誰,反正都擠。”韓松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曾說,“你以為這只是地鐵,其實它就是北京。”
雖然現在更喜歡開車,但每個星期二早上去公司開會的時候,趙罡都還要從宋家莊坐地鐵到王府井,“時間上最靠譜,也不用擔心找不到停車位”。他說,路上他也會看看廣告,但那就像是審查孩子作業的家長一樣,他沒有辦法欣賞廣告背后有什么美學隱喻,他的注意力更多在于燈箱有沒有亮,廣告有沒有貼錯?
而這也已經是張星海拍攝北京地鐵的第九年了。“作為一個攝影師,我能做的僅僅是把地鐵里的喜怒哀樂記錄下來,提供一份真實的當代影像檔案。”張星海在他的拍攝筆記中這樣寫道,“也許,50年、100年后,當人們看到這些照片時,他們會說,哦,原來我們過去是這樣生活的。”
在張星海的照片里,當穿著職業裙裝的年輕女孩拎著高跟鞋,垂著頭光著腳疲憊地走在站臺上,她也許不知道周圍這些精心安排的驚喜,至少在她對面的廣告燈箱里,784盞LED燈正在試圖為她創造一個“正午12點的太陽”。她只是跟其他1000萬人一樣,擠在混雜著汗味的北京地鐵里其中一人。
早上4點45分,第一列北京地鐵從回龍觀東大街站出發,開往南鑼鼓巷。20分鐘內,北京的地下世界又復活了,大部分的地鐵站駛出首班車,又會有新的乘客走進地鐵,新張貼的廣告將繼續試圖搶占他們5秒鐘的注意力。
但并沒有多少人知道,為他們塑造這個商業世界的人們,正在早上補覺。地鐵仍以每小時80公里的最高時速向下一個目的地沖刺,帶著搖晃車廂中的城市人,在“歡迎乘坐北京地鐵”的地鐵播報聲中,穿梭在這個密布著白日夢想的地下世界。
(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